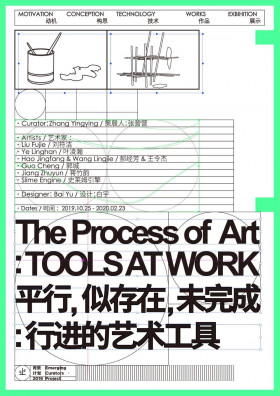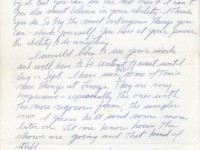索尔•勒维特——从凯奇,激浪派和极简主义谈起
索尔·奧斯特洛(Saul Ostrow)
一路行驶至康涅狄格州的乡下,来采访索尔•勒维特。他和他的妻子以及女儿们住在那里。一旦机会成熟,很多与极简主义关系密切的艺术家们就会想法设法地逃离被当代艺术所充斥的都市环境。这不由引起了我的思考,极简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以及勒维特的作品在其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复杂而自相矛盾的角色。
亲历一个时代所带来的乐趣之一是,当你翻开历史书时,一看就知道上面哪些干净整齐的事件记载是被去除了旁枝末节修改过的,哪些记载是与事实有偏差的。早在六十年代我是纽约一个艺术学生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勒维特的大名了。当时他是极简主义艺术家的核心之一,他们当中还包括了雕塑家唐纳德•贾德 、丹•弗莱文 和罗伯特•史密森 ,以及画家乔•贝尔 、罗伯特•莱曼 和罗伯特•曼戈尔德 。他们的创作具有一种一丝不苟的工业审美和简约特质,这一特质使他们的作品看起来高度非个人化,智力化且城市化。然而之后,勒维特从系统性物件(systemic objects)的创作转向最终只被简单称作壁画的墙上绘画(Wall Drawings)。他用图纸,图表和指令来强化那些界定他创作的观念,以及可以体现艺术家本人品味和审美本质的那些决定——就勒维特而言,这些决定是由受委托来完成他作品的技师们所作出的。
索尔•勒维特的创作引发我们对语言世界,物体世界及行为世界之间的差异性的关注。通过关注他们之间的断裂离析,勒维特在极简主义和观念艺术间的缝隙上架起了一座桥。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既致力于让艺术作为世上一件简单的“物”而存在,又想方设法让艺术“去物质化”。尽管勒维特近二十年的创作始终以“什么可以被讲述”和“什么可以被呈现”之间的关系为前提,他现在创作的壁画,墙上绘画和雕塑在形式上越来越“古怪”,在实现方面也越来越凸显个人风格。我们在镇上的一家小餐厅用了午餐,拜访了他在当地设计的一座犹太教堂,又参观了一间存放其大量艺术收藏的库房之后,索尔•勒维特和我回到他舒适的起居室,开始回顾过去,着眼当前。
索尔•奥斯特洛(以下称为SO)
你对艺术的思考会不会同约翰•凯奇 的谱曲,与他的偶发音乐有关?凯奇似乎对很多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艺术家来说都是一个关键人物。
索尔•勒维特(以下称为SL)
六十年代早期是一个关键时期。约翰•凯奇的思想来源于杜尚和达达。我对其并不感兴趣。我的思考来源于迈布里奇 ,和从音乐里来的“系列性”想法。我认为达达从根本上说是“感知的”(perceptual),它往往依赖于观众被激怒的反应。波普艺术是对这一志趣的继承。而我对讽刺不感兴趣;我想要的是强化“观念”在艺术创作中的首要地位。我的兴趣,从1965年左右开始,在于建立产生自极简艺术的观念系统(conceptual systems)。基本上这是对杜尚派美学的抛弃。
SO
我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凯奇后期的一些作品就只是给表演者一些指示,就像你在你的“指示类作品”中所做的那样。这个想法看上去是从凯奇开始,到激浪派,再到极简主义者,然后再到观念主义者。
SL
在我之前,激浪派 的观念主义是受杜尚的影响。我的思考是对他们想法的一种回应。极简主义无论怎么发展,我都不认为它是作为一个想法而存在的。它只是在风格上对抽象表现主义修辞的回应。它是自我毁灭(self-defeating)的,因为形式的简化只能走这么远。一旦达到了最简单的形式,它就结束了——例如罗伯特•莫里斯 1964年在格林画廊 展出的多面体装置,或者劳森伯格 的白绘画(White paintings),当然,尽管罗伯特•莱曼仍可以以很好的深度和灵感继续白绘画创作。就我来说,我使用这些简单形式的元素——正方形,立方体,直线和颜色——来制造逻辑系统。这些系统中的大部分是有穷的,也就是说,一旦达成所有可能的变化,它们就是完整的了。这让这些系统保持简单。
SO
我们可不可以回到刚才,谈一谈莱曼和唐纳德•贾德的差异?一方面,莱曼,他有一个关于“系列”的无穷系列作品。贾德与之相反,他系统化了一个关于“多样化”的无穷系列。
SL
这是他们在走进极简主义的死胡同后的反应。一个是去使用新的材料。贾德用胶合板和镀锌金属,而弗莱文用荧光灯管。就像你说的,他们“系统化”了一个关于“多样化”的无穷系列,想想弗莱文的“塔特林 ”作品吧。同样是运用序列系统,贾德用在了他的渐进作品中,弗莱文用在他的“公因数三 ”中。对极简主义死胡同的另一个回应是强调“过程”这个观念,单纯的绘画行为,在这方面莱曼是最好的例子。
SO
你在那样的情形中处于什么位置?
SL
我同时涉足于观念和物体,但不去利用新材料和行为的过程。我通过使用基本形式来形成构思的过程,对“系列的想法”(serial idea)的运用变成了我的词汇。
SO
一旦你开始“系列地”创作,有一些决定就被妥协了。比如说你的墙上绘画,本来就只是一组指示。把脚本交付给另外一个人,实际上就给这组描述带来了更多的变数,这一举动会被解读为作者意图“去美学化(de-aestheticize)”这个作品,或者至少使艺术家保持与作品的距离,以使作品不受艺术家本人的趣味所主导。我自己也曾经做过一次你的墙上绘画。你给了我一些指示,上面写着“用铅笔,在一个10英尺见方的区域内,每天随机画1000条长度10英尺的线,画十天”。这些线条如何分布在这个方形区域内则完全取决于我的意愿。而我不知道你想让它们被画成什么样子。
SL
它看来什么样子并不重要。只要你是随机在这个区域内展开的,你怎么做都无所谓。在很多的墙上绘画中,只留有很少的余地让绘图员做变动。但是无论如何很显然,在视觉上,不同的人做出的作品是不同的。我在一些其他的作品中,给了绘图员非常大的发挥空间。对以这种方法实现的作品来说,作品的外观较之于作品的想法是次要的,这样凸显了想法的首要性。“系统”就是艺术作品本身。作品的外观是对这个“系统”的验证。缺少对系统的理解是无法理解它的视觉外观的。“是什么”才是根本上重要的,而不是它看起来是什么。
SO
在1961-1962年,艺术创作的可能范围是从第二代抽象表现主义,到波普艺术到激浪派的。因为什么观念艺术最终如此吸引你?比如说,莱因哈特 在你的思考中扮演个重要角色么?
SL
当然。莱因哈特是个富有想法的艺术家,并且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的写作非常有意思,就和他的艺术一样。事实上,他的例子提供了另外一个方向:非波普艺术和激浪派,而是一种更具有生命力和更多产的方式。他的艺术的确成为了我的思考的关键。
SO
在观念主义思想的演化过程中,罗伯特•史密森和丹•格雷厄姆 扮演的角色有多重要?我知道梅尔•博赫纳 和史密森有很多共同的想法;丹是中心,他开了丹尼尔画廊,推介了很多我们今天聊到的艺术家。我一直把丹看作观念和极简艺术中的乔治•麦素纳斯 。我记得那些丹展示作品的周日聚会,我在其中一次聚会上看过他的云电影(Cloud movie),和一件他用天空的照片做的装置作品。那是一个重要的聚会场所。
SL
丹•格雷厄姆是个辩论家。他和史密森俩都爱泡在“马克思的堪萨斯城”酒吧聊天。某种程度上,这也算是他的艺术形式。当我第一次遇见他时,他正在用打字机的纸做一件极有意思的作品。他的头脑很棒。他比任何人都早很久开始创作这些。这件作品是我见过的最早的“非杜尚派”式的观念艺术。它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罗伯特•史密森最有意思的作品是他的写作。即使他做重要的装置和大地作品,但他的写作是负有远见和特立独行的。总的来说,他的认知是更倾向于文学性的,他可以在写作中真正地表达自己。如果他活得再久一些,我觉得他会拍更多的电影。那是一个可以让他更好地推进自己的想法的形式。梅尔•博赫纳也参与了史密森的写作,曾经共同署名一件作品。在梅尔进入他更重要的使用数字和测量的作品之前,他们就曾一度在彼此的想法中汲取养分。
SO
那赛斯•西格尔劳博 呢?你和卡尔•安德烈 参加了包括“影印书本 ”在内的一些赛斯早期的项目。这些项目在极简艺术和观念艺术之间的间隙上搭建了桥梁。
SL
赛斯对于约瑟夫•科瑟斯 ,劳伦斯•韦尔 ,道格拉斯•许布勒 ,和罗伯特•巴里 的支持是有重大意义的,尤其是在当时。这些艺术家中,每一位都用观念主义的不同工具创作出非常好且持久的艺术作品。在随后的几年里,他们都扩展了自己的的想法。
SO
那么,后来作为后极简主义和反形式主义而为人所知的那些艺术家呢?
SL
极简主义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想法——它在开始前就结束了。许多不同类型的艺术家开始用简约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意图。几乎每个60年代到70年代的艺术家都离开极简艺术往不同方向发展。如果你不想参与到杜尚派式的思考或者波普艺术的话,那就没其他地方可以开始了。这些不同的逃生路线终于形成了经典的观念艺术,最终在80年代到90年代全都融合在了一起。这主要归功于将这两种思考方式合二为一的布鲁斯•瑙曼 。
SO
那罗伯特•莫里斯呢?他跟观念艺术关系较浅,是因为他来源于杜尚,新达达么?
SL
他的作品更像是挑衅。他把极简主义带到了它的逻辑终点。许多他早期的作品是杜尚派的。
SO
我对你的作品中,在我看来是隐含的和显现的政治感兴趣。许多是把“艺术的去物质化”用作策略。另一方面,我仍还有一件用250美元买来的你的折纸作品,据我所知,由于你给这些作品制定的一项条款(条件), 现在它仍然只值250美元。 这显然表明了你对于艺术的商品化和它们的增值模式的关注。
SL
60年代被各种政治和革命所淹没。当然不仅仅在艺术领域,还有女权主义,种族平等,反战等。我,就像我认识的几乎所有的艺术家一样,都参与了所有这些运动,并且在政治上都是左倾的。其中一个想法是将艺术作为商品?。我想通过在墙上绘画, 使其不可被移动——这就意味着拥有者对作品有某种‘承诺’,作品也就没那么容易被买卖。我也做了一定数量只卖100美金的作品——不是250美金,你被打劫了。这是一些地图、手绘或剪切的明信片、揉皱的纸、折纸、撕碎的纸等等。并且,因为墙上绘画是根据写好的指示画出来的,任何人都可以画,不管多糟糕。就像每个人都可以轻易拥有一个自制的弗莱文(Flavin)作品一样。从1965年起,我开始对制作书籍感兴趣 。当我做“系列计划 #1”时,我决定要做一本解释作品如何被理解以及系统如何运行的小书册。这是我第一次想要做一本自成作品的书籍而不是目录。在大多数这些书中,我使用很多照片。这其中埃德•拉斯查(Ed Ruscha) 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买书是一种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很小的代价获取艺术作品的方式。
SO
我认识个人在阿姆斯特丹为她自己做了一幅墙上绘画。 她有一整套可以拿来重新制作的作品收藏;她还有一件弗莱文(作品)和一幅诺兰的条纹绘画。你是否觉得“民主的艺术”的概念正在成为极简主义和观念艺术二者发展的一个显著方面?是它促使你在近年来做公共艺术项目?这是你作品中的政治部分吗?
SL
这是其中一方面。是质疑 “艺术是难以接近的” 这种通常看法的一种方式。就像大地艺术和装置艺术的发展源于“让艺术走出画廊”的想法,我对公共艺术参与的基础是墙上绘画的延伸。一旦开始在墙上创作,要使用整面墙的想法就随之而来。这意味着艺术密切参与了建筑,可以被每个人看到。这就避开了画廊或美术馆的贵重设施。并且,因为艺术是一个通过形式来传达想法的载体,形式的重新制作强化了想法。被重新制作的是想法。任何人理解了艺术作品也就拥有了它,我们都拥有蒙娜丽莎。
SO
你认为极简主义者和观念主义者们把他们自己看作是在拯救艺术,而不是把它带向终点么?
SL
作为一个50年代后期的艺术家,我知道当抽象表现主义成为主流形式,一时间大量的作品被创作出来时,终点就是可见的了。可能是因为代沟的原因,我知道我不想那样做。那是一种我不能接受的形式。我没想要拯救艺术——我太过于尊重老艺术家了,以至于我不认为艺术需要拯救。但我知道它结束了,即使如此,那时,我并不知道我会做些什么。每一代人都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自我更新;永远会有对彼时标准的反抗。这是可以预见的。 我认为六十年代的艺术,无论是杜尚派还是非杜尚派,都有其价值的原因, 是因为它们把艺术从形式和美学中解放了出来。它允许艺术迈向叙事性,而不受限于现代主义的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艺术变得政治化了,之后社会化了,再之后性感化了。
SO
这种现代主义的唯美主义是以格林伯格(Greenberg)所代表的么,总体来说?
SL
格林伯格是起始于罗杰•弗莱(Roger Fry)和早期现代的那种唯美主义的最后遗老。他厌恶极简主义。尽管就修辞方法来说它仍然是一种形式主义,它结束了现代主义。话说回来,极简主义的问题在于它成为了自我的终结。而观念艺术使它从“形式”和“感知”中逃脱出来,进入到“观念”和“分析”中。一个想法一旦被学院派编进教科书里就完了。格林伯格(Greenberg)对第二代抽象表现主义运动的拥护就是它的死亡之吻。
SO
你把你的创作看作一种抽象的叙事,就像讲述一个关于排列组合,或关于语言与物体之间差异的故事么?语言对你的作品有多重要?
SL
序列系统和它们具有叙事功能的排列组合应该被理解。人们总是把东西看作是视觉物品而没有理解它们到底是什么。他们不明白尽管视觉上可能乏味,但是有趣的是叙事。它可以被当作一个故事来解读,就像音乐可以作为时间中的形状被聆听。跟文学比起来,系列性艺术作品的叙事性更像音乐。词语是另外一回事。在70年代期间,我对使用词语和词义来进行艺术创作感兴趣。我做了一组 “位置”作品(location pieces)来引导绘图师做艺术。导向最终图像的所有路径都被显示出来。人们可以解读这些导向并且验证其过程,甚至做出这个作品。
SO
这就不由得让我们想问,你如何让它一直有趣,如何让它一直感动你自己?
SL
除非你去思考你正在做什么,不然最后你总会发现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做着相同的东西,接着你就觉得枯燥乏味,最后充满挫败感。 艺术家做艺术创作的时候,他们不应该考虑是否可以做这个或那个。就我而言,我到达了我作品演进的一个节点,我的意识形态和想法开始成为束缚。我感到我变成了自己声明的原则和想法的囚徒。我发现我被作品中已有的逻辑强迫着走上了另外一条路。这到底算进步或是退步或是侧步其实无所谓。那个时候我搬到了意大利。十五世纪的意大利艺术让我印象深刻。我开始思考艺术怎么不是一个前卫的游戏,它应该是某种更普世,更重要的东西。
SO
所以从某个角度上来说,你做的是“解放”,然后它变成了束缚,接着你不得不把自己从自己的牢房中解放出来。
SL
你不该成为你自己想法的囚徒。每个人进入自己的“盒子”里,宣布原则——但愿他们是真心的——你有你认为正在遵循的“约束”和“结构”,接着你意识到你所说的是:“我可以做这个,但是我不可以做那个。” 然后在某个时候你会说:“那么,为什么不呢?” 而答案是:“因为我告诉过自己我不可以。”如果你不停地告诉自己:“你可以。” 那你就解放了。如果你彻底被限定住了,那么所有留给你做的就是打碎模子。“每堵墙都是一扇门。”
SO
评论家和史学家们不喜欢艺术家这么做——这毁掉了他们已经连续地投入讲述了很久的故事。
SL
艺术家教评论家去思考什么。 评论家重复着艺术家教他们的东西。如果之后你说,“噢,这些不再管用了。” 他们就会感到极为不安。不过这也是预料之中的,因为他们就得学点其他东西。学院派就爱学院。
SO
在八十年代中期,色彩进入了你的创作。有些人把它看作装饰的或者说是一种唯美主义的回归。
SL
当我刚开始在墙上创作绘画时,想法的逻辑就接管了(作品的创作)。从线条到形状,从平面到立体,你没看错,还有对颜色的使用。可能在有的人看来,颜色等同于装饰,但是我试图客观地使用颜色。起先我使用彩色墨水,从三原色开始。色彩原理表明, 所有颜色都可以由三原色和黑色的混合得到。之后我改用丙烯颜料,外加三个间色——绿色,橙色和紫色——但是不混合它们。我不为效果而使用颜色,虽然我不觉得这是件坏事。亚伯斯(Josef Albers)使用颜色就追求它最极致的效果。
SO
我还在想那些有许多奇特的形状和一个底色的墙上绘画和壁画,它们的颜色似乎是随意的。你在这里似乎引入了随意元素的想法?
SL
在我看来,我的作品都是以一种逻辑和有机的方式来进行的。每一步演化都会导向下一步。或许有时两步之间有一个跳跃,但我不认为这是一种随心所欲。当我写《关于观念艺术的句子》的时候,其中第一句就是说艺术家不是理性的,而是能跳跃到新想法上的。所以,我希望这么做。有些时候,这样做可行,有些时候不可行。但即使不可行,也可能带来某种可行的东西——一个启发。身处墙面尺寸的空间工作时,空间的特殊形状会给我一些想法。
SO
作为一名观众,我对你最近的作品有种印象——比如那些波浪线水粉——看来你真的是在重新评估那些曾在你创作更系统化,简单化的作品时的背景部分。这算不算是过去(的元素)作为一种更合用的东西回归了?
SL
我近期的做的那些水粉作品源于一些早先的墙上绘画,用的是非直线的铅笔线条。我一直在做素描,后来是水粉,同时还有墙上绘画。现在墙上绘画越来越多地由别人来完成。就像墙上绘画,水粉画有着它们自己的有机发展,我试着把它们看作我自己生活中的老伙计。我后来找到了大张的纸,五英尺宽,允许我画比较大的作品。水粉画中的想法和墙上绘画的不能并行。他们非常不同,遵循各自的逻辑。墙上绘画有可以传达的想法而可以由他人来实现。水粉则只能由我来画。
SO
劳伦斯•韦纳(Lawrence Weiner)曾经跟我说过,艺术创作就是一个不停重新修改的过程。
SL
就我的情况来说,经常是厌恶。当我看到我做的东西的时候,我无法忍受。当一件作品做完,我就继续做下一件。我总觉得下一件会比我之前做的好很多——一个补救的机会,一个可以抹掉过去奔向光明未来的希望。当然,这样的好事从来没发生过,但它促使我不停地做下一个。
SO
你最近的雕塑——混凝土装置作品和砖造的半球体——已经在规模上变成建筑了。这又给了你另外一个可供把玩的变量么?
SL
尺寸和规模的问题至关重要。我认为每个想法都有一个最佳尺寸。太大,就变得华而不实和浮夸。而太小,就会成为一个物件。当作品完成的时候,它的尺寸是否合适就显而易见了。我一直把我的三维作品称作“结构”,因为我的想法更多是从建筑史而非雕塑史中获得给养。我感觉离布雷(Boullee)要比离卡诺瓦(Canova) 更近。但是我并不想要成为一名建筑师。我离建筑最接近的是在切斯特市设计的我们的当地犹太教堂,我把它看作是几何形体在一个符合仪式功能的空间中的问题。在这个例子里,我和建筑师史蒂文洛伊德(Steven Lloyd)一起工作,他了解很多我不知道的事。但是关于形体的主要想法被保留了,并且我觉得创造出的空间就是我所希望的那样。
SO
许多人认为,极简和观念艺术对艺术变得不再重要的处境做出了“贡献”,因为艺术变成可以是任何东西,并且什么都是艺术。你认为它的影响是什么?
SL
极简艺术没有出路。观念艺术变成了一个解放,给未来40年艺术提供了真正的推动力。当今所有重要的艺术都源于观念艺术。这其中包括了装置艺术,政治艺术、女性主义艺术和社会导向艺术。另一个重大的发展发生在摄影领域,不过摄影同样也受到观念艺术的影响。
SO
如果你可以给《关于观念艺术的句子》(“Sentences on Conceptual Art”)做一些补充或者修改,你会做些什么改动?你是否打算写一篇新的文章来表达你的观点中那些看起来比较重要的变化?
SL
我觉得那些《句子》没有问题。尽管它们针对60年代的艺术,但仍然符合我现在的想法。我不会删减或增添任何东西。当今的艺术比以前更加宏大和繁荣了,但是艺术思考的过程并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只是强调的重点变化了。
SO
我想是阿多诺(Adorno)说过艺术的敌人是平庸。
SL
(艺术)是不可以无聊。
——索尔•奥斯卓是克里夫兰艺术学院的美术学院院长和油画教授,同时也是艺术家、评论家、策展人,以及《BOMB》的主编;他同时还担任路西塔尼亚出版的联合编辑,主要发表文化方面的文集;以及由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出版的《艺术、理论和文化评论之声》系列丛书的编辑。奥斯卓为大量刊物撰文,其中包括《今日艺术》、《艺术杂志》、《艺术快讯》、《新造型艺术》、《艺术国际评论》和《新艺术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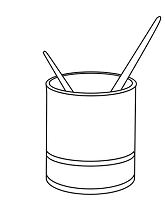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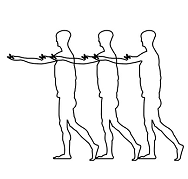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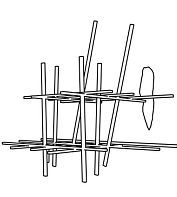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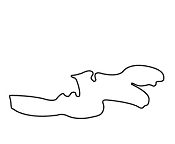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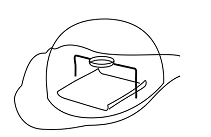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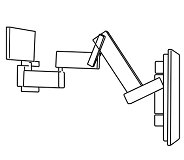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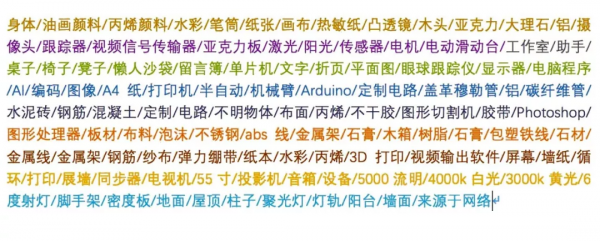
 Fr
Fr En
En